 特雷德金。 |
当美国联邦调查局(FBI)告诉我们,家长们需要准备花费高达650万美元,各方打点,才能让孩子进入名牌大学时,这似乎意味着,美国大学一切都很正常、非常好,但沃伦·特雷德金告诉我们,这是一种幻觉。
他是圣路易斯大学拜占庭历史的杰出教授,曾任教于伯克利大学、佛罗里达国际大学、希尔斯代尔大学、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。1967年进入大学后,他凭借长期的经验,对美国最彻底的左翼主要机构提出指控,并提出补救措施,他的书《我们需要的大学》(The University We Need, meet, 2018)以深入浅出的方式阐述了这一观点。
特雷德金说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:教工委员会按照惯例应该筛选出最有能力的候选人,却因为害怕自我暴露,他们有可能会拒绝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。而且,他们通常只青睐"黑人、西班牙裔和女性申请者,这些人的观点同大学主流相契合"。毫不奇怪,研究生们会准备一些晦涩难懂的专业论文,希望凭借"很少的时尚出版物"赢得这种懒惰委员会的青睐。教授们贿赂成绩好的学生以赢得他们的正面评价,管理员(即最近几十年,对教学和研究不感兴趣的教授)人数翻了一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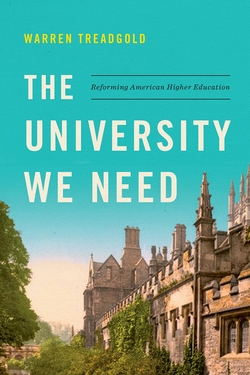 《我们需要的大学》封面。 |
更糟糕的是意识形态塑造的集体思维:"主流观点认为,与种族主义、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压迫作斗争是如此重要,以至于它取代了一切"——包括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对年轻人的适当教育(导致"无关学科的平庸课程")。左派教条——坚持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过去,颂扬所谓的被压迫群体,用"叙事"取代事实,在"社会正义"面前卑躬屈膝——几乎占据了所有高等学府的主导地位。
特雷德金认为,所有这些都很重要,因为从大学开始的东西会传播到整个国家;看看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或众议院激进的民主党就知道了。事实上,"我们需要好的大学,就像我们需要可靠的电力和安全的饮用水一样。"
但是到哪里去找呢?正如波士顿大学(Boston University)的约翰•西尔伯(John Silber)从惨痛的教训中学到的那样,试图修复现有机构的努力失败了;无论一个校长多么敬业、多么能干,他都无法让一所大学转向,相反,Treadgold设想从零开始建设一所新的大学。
这所新大学将以真正的明辨为特色,而不是留在安全区;雇佣临时管理人员,而非长期管理人员;培养卓越而非不合格学生;强调思想的多样性,而不是肤色;博雅教育,而非特殊的课程("木乃伊、僵尸和吸血鬼",这都什么鬼?);出国游学,而不是去国外校园;专业扎实,而不是跨学科的研究;真正的学术,而不是后现代的哗众取宠。
 UCF课程描述"木乃伊、僵尸和吸血鬼"。 |
特雷德金的设想甚至包括了一些最小的细节:在他计划中的校园里,"窄床""应该有助于阻止学生留宿过夜"。他建议在华盛顿特区外25英里的地方,建设可以直达权力中心的走廊通道。
 狭窄的宿舍床。 |
特别有趣的是,他呼吁将重点放在其他大学避免讨论的话题上,比如"气候工程、家庭破裂的后果、集体犯罪的哲学矛盾"。他预测,这些新手将挑战所谓精英大学的古板,打破现状,创造新的质量标准。
在另外的分析中, Frederick M. Hess和Brendan Bell做了计算,结论是这样一所大学的建造和永久捐赠将耗资34亿美元,这是一笔庞大的捐赠,但2017年捐助者向高等教育捐赠了436亿美元。34亿美元也只是一些保守派巨额财富的一小部分(你好查尔斯和大卫,你好谢尔顿,你好鲁伯特)。无论是单个还是联合捐助,他们都可以用19世纪那种宏大的风格,资助书中提到"我们需要的大学"。
如果这一计划戏剧性地打破先例——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一所大型私立研究型大学成立——它的潜在影响可能会激发人们打开自己的钱袋子用以资助。 特雷德金认为:"如今,任何捐赠人都应该考虑资助一所新的一流大学,能够为社会、文化或政治带来长期影响。"但这必须尽快着手,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;学者如果在这个机构任职,要么他们是退休,要么是去世,而不是被他人取代。
 1890年芝加哥大学成立。 |
《我们所需要的大学》是一支力图延续美国高等教育辉煌传统的强大力量,但它会找到观众吗?更具体地说,保守的亿万富翁们会响应特雷德金的号召吗?
Pipes先生是中东论坛的主席。© 2019 by Daniel Pipes版权所有。
 《华盛顿时报》的插图。 |

